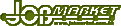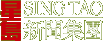迷失身分漂泊无根「港漂自白」:在香港做人很辛苦!近年由于D&G事件、双非孕妇问题、北大教授孔庆东骂港人是狗等争议,令酝酿已久的中港矛盾一发不可收拾,内地人被视为争资源、抢饭碗的一群,更被部分港人标签为「蝗虫」。 偏偏从内地来港的「港漂」与日俱增,各人怀着不同原因漂泊到香港。有曾在美国留学的「海归派」,跟随港人丈夫来港定居,备受港人孤立排斥;有来港读博士的初生之犊,受本地自由和公平的环境吸引,对未来充满憧憬;也有清华尖子在商界经历迷失自我的疯狂加班岁月后,重拾勇气追求梦想。 也许仇恨源于恐惧,惟有彼此了解,中港两地的人才能「大和解」。三个「港漂」,三个离乡别井的故事,让港人从另一角度窥探内地人真实的一面。
海归派:「对香港最没归属感」
三十五岁的车华,是其中一只惊弓之鸟,但因抵不上记者死缠,才心软受访。操着半咸淡广东话的她,身穿OL套装,谈吐举止温婉优雅,与内地游客无礼粗鲁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。 「在香港,行为举止要很谨慎,在公众地方不会大声说话,在地铁不会进食。想向港人展现自己是个有质素、认真工作的内地人典范,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我。」她小心翼翼道。 车华是广西柳州人,自小品学兼优,国画尤其出色,初中已在北京开画展。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,在深圳一间大型金融证券公司任职三年,已储够学费赴美进修会计硕士,成功晋身四大会计师行,在纽约曼克顿上班,年薪约四十万元。三年前,她与在美国留学的港人丈夫结婚,决定来港定居,并向公司申请调职到港。当时她已留美六年,尚差一、两年便可取得绿卡。
放弃绿卡随夫来港初到香港,她没有言语不通的问题,反而居住环境令她吃惊。 「最初和丈夫同住大埔五百呎居屋,睡房只有八十呎,感到很压迫,因在广西一间屋有九百呎,去年底才搬到将军澳九百呎单位。」工作地点由纽约曼克顿变成中环,雇主虽然没变,但生活步伐和工作气氛却差天共地。 「不太relax,香港人行路好快,人也变得急躁。」由于工作繁重,她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。 「亚洲人很勤力,香港的工作量是美国的三倍,好辛苦。」
好心相助不被领情勤奋和拼搏,是内地精英的特质,车华也不例外。最初在美国搵工,她与内地同学一起研究如何写求职信,互相进行模拟面试,结果她成为公司唯一获聘的内地人。工作遇上不明之处,她会不耻下问;哪个部门需要帮手,她会主动协助,是上司眼中的优秀员工。来到香港,她顺理成章获擢升为部门经理,下属多是本地人,不免视她为竞争对手,保持距离。 「以前在纽约,同事关系很融洽,但现在同事关系疏离,会刻意孤立我。即使我主动帮忙,他们也觉得我是扮好心。」近年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白热化,车华眼见不少同胞被排斥,心里很不是味儿。 「在广州人和美国人眼中,我也是外来人,但他们很包容,从没歧视我。可是在香港,虽然有丈夫在身旁,却是令我最没有归属感的地方,在香港做人好辛苦,不论在公司或生活当中,也不停提醒我只是个外来人。」
初生之犊:「这里令我心境平和」
「香港只是我暂时居留的地方,毕业后想到美国实验室做博士后深造,然后希望可再返香港的大学,从事学术工作。」这是徐敏的梦想,但从前,梦想离她很远。她生于广东清远的穷乡僻壤,父母为赚钱供书教学,每天站立十多小时剪布缝线。 「父母辛劳的付出,只为我们日后过得好。清远的教育资源有限,只有三分一人可升读高中,所以要努力读书,才可出人头地。」自小看电视节目《闪电传真机》长大的她,从没想过有天来港读书。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,一次偶然机会下协助港大教授当研究助理,才萌生来港读书的念头,申请两次才成功,「我是家乡第一个出产的博士研究生,每次有客人到访,父母就会欢天喜地炫耀一番。」
醉心研究回馈港人
本港生活难适应易自杀
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耿春亚指出,自从○八年放宽留港政策后,五成内地生会留港工作,当中两成持续工作三年以上已取得香港身份证。不过,内地生来港要面对适应问题,过去十年就有七名内地生自杀身亡,耿春亚认为,部分内地生不懂说广东话,因此不敢主动与人倾谈,以致孤立自己,加上他们的自尊心强,难以融入本港生活。 「个个都是内地尖子,自小活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下,当来港遇上挫败,心理无法调节,便容易产生怨气,孤独感和漂泊感都很重。」清华尖子:「香港是第二故乡」踏入七月,刚好是赵晗来港满七年的日子。她与徐敏同龄,但在香港的时光,已叫她饱尝人生跌荡。十九岁时,她放弃内地学生趋之若鹜的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系学位,来港大修读会计系,但成为会计师并非她的理想,只是盲目追求主流价值观,却把她推到情绪低潮。 赵晗出身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让她自由发挥。她生性聪颖,入读北京最好的高中。在港大三年,赵晗每天与讨厌的数字搏斗,毕业后投身四大会计师行当核数员,没料到竟是疯狂的加班生活。 「每晚做到凌晨,有时甚至通宵,星期六、日也要工作,那是毫无底线的加班。点解香港人可以忍受到?他们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抓住,好无自由,究竟是为了什么?」挨了七个月,纵使要面对失业的忧虑,赵晗终抵受不住辞职,「挨不去的痛苦,已大过我改变的痛苦。离职那天,同事都为我拍掌,对我来说是celebration,终于可以向主流say no!」
重拾梦想追求公义离职后,身边朋友都劝她尽快找工作,才不致要返回北京,但她反问:「为什么不可以回北京?」可是她渐渐感到迷失,「约旧同学出来,个个高薪厚职,但我什么都不是。」对于自己的身分,充满疑惑。 「来了香港数年,我算是香港人吗?但我对北京愈来愈陌生,又算是北京人吗?那种不知自己是谁的感觉非常差,像个无根的人。」浮沉数月,赵晗在朋友介绍下加入突破机构,服务北京农民工子弟接触有关双重身份问题,令她茅塞顿开。 「好多北京农民工留京多年,但没有北京户籍,不敢自居为北京人,但他们可视北京为第二故乡。我也不一定只有一个身份,可以是北京人,也是香港人,可以视香港为我的第二故乡,不再是过客。」寻回身份认同,赵晗也重拾追求梦想的勇气,就是为北京农民工争取公义。 「中国发展得太快,产生很多问题,北京农民工为城市付出许多血和眼泪,但为何他们的子女不可在城市读书?最有头脑最有才华的人,应该走到最无资源最穷最无公义的地方,而不是只服侍最有钱的人,那才有意思。」 |



 「港漂」原本泛指漂泊到港的异乡人,惟近十年来港读书及就业的内地尖子与日俱增,「港漂」已成为他们的专有名词。邀请「港漂」接受访问非易事,皆因他们被传媒的负面报道吓怕,担心与「蝗虫」扯上关系;也怕锋芒太露,会树敌更多。
「港漂」原本泛指漂泊到港的异乡人,惟近十年来港读书及就业的内地尖子与日俱增,「港漂」已成为他们的专有名词。邀请「港漂」接受访问非易事,皆因他们被传媒的负面报道吓怕,担心与「蝗虫」扯上关系;也怕锋芒太露,会树敌更多。 相对车华的迷惘,廿六岁的徐敏有如初生之犊,对未来充满憧憬。两年半前,她考获奖学金到港大语言学系修读四年制博士课程,并入住附近的明爱宿舍。宿舍月租四千元,只有约五十平方呎,电视机、雪柜、睡床及衣柜都是袖珍版,徐敏的衣服和杂物也要随处挂;一室简陋,尽显她「漂」的状态。
相对车华的迷惘,廿六岁的徐敏有如初生之犊,对未来充满憧憬。两年半前,她考获奖学金到港大语言学系修读四年制博士课程,并入住附近的明爱宿舍。宿舍月租四千元,只有约五十平方呎,电视机、雪柜、睡床及衣柜都是袖珍版,徐敏的衣服和杂物也要随处挂;一室简陋,尽显她「漂」的状态。 初到香港,在徐敏眼中,万事万物皆美好。 「无论搭巴士、购物、去银行及邮局都好有秩序,职员态度友善,服务专业,不像内地职员态度恶劣,问什么都说不知道,而且食品很安全,不用担心有害。每次由内地过关到香港,心境也会变得平和。」香港讯息自由,对她而言尤其珍贵,「内地只有一种官方讲法,只知不是真相,但不知真相如何。但在香港没有限制,可听到不同声音再自行判断,而且很可靠。」走入港大校园,虽然与本地同学的话题南辕北辙,但单纯安静的研究环境,令徐敏相当惬意。 「在内地做研究,虽然有好多资源,但要打关系、应酬才可申请到经费,香港环境则很公平,毋须为争取利益而扭曲自己。」不过作为内地人,难免也曾被歧视,试过在校园遇上老伯骂她争夺香港资源,但徐敏没放在心上,皆因她相信自己将来可为港人带来贡献,令港人改观。 「每个研究都有意义,到最后会有应用的价值,所以我会畀心机,希望尽快发表属于自己的研究报告,为社会带来贡献。」
初到香港,在徐敏眼中,万事万物皆美好。 「无论搭巴士、购物、去银行及邮局都好有秩序,职员态度友善,服务专业,不像内地职员态度恶劣,问什么都说不知道,而且食品很安全,不用担心有害。每次由内地过关到香港,心境也会变得平和。」香港讯息自由,对她而言尤其珍贵,「内地只有一种官方讲法,只知不是真相,但不知真相如何。但在香港没有限制,可听到不同声音再自行判断,而且很可靠。」走入港大校园,虽然与本地同学的话题南辕北辙,但单纯安静的研究环境,令徐敏相当惬意。 「在内地做研究,虽然有好多资源,但要打关系、应酬才可申请到经费,香港环境则很公平,毋须为争取利益而扭曲自己。」不过作为内地人,难免也曾被歧视,试过在校园遇上老伯骂她争夺香港资源,但徐敏没放在心上,皆因她相信自己将来可为港人带来贡献,令港人改观。 「每个研究都有意义,到最后会有应用的价值,所以我会畀心机,希望尽快发表属于自己的研究报告,为社会带来贡献。」 自九九年起,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推出招收内地本科生试验计划,每年提供一百五十个名额,从此开启「港漂」之门。至○八年,港府推出「非本地毕业生留港/回港就业安排计划」,容许在港内地毕业生可无条件留港一年,令来港内地生人数急升,去年就有近一万三千名内地生赴港留学。
自九九年起,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推出招收内地本科生试验计划,每年提供一百五十个名额,从此开启「港漂」之门。至○八年,港府推出「非本地毕业生留港/回港就业安排计划」,容许在港内地毕业生可无条件留港一年,令来港内地生人数急升,去年就有近一万三千名内地生赴港留学。